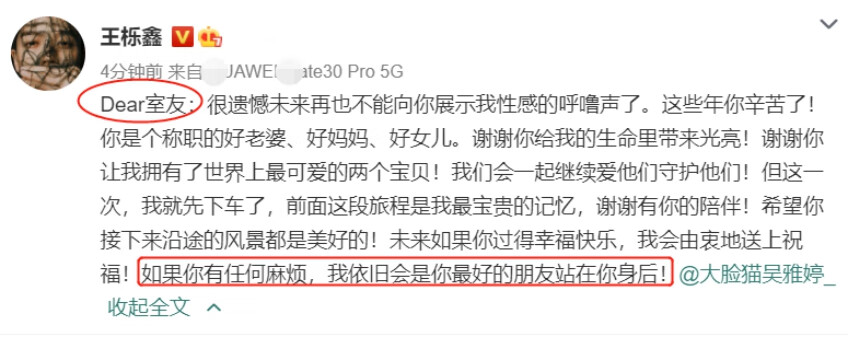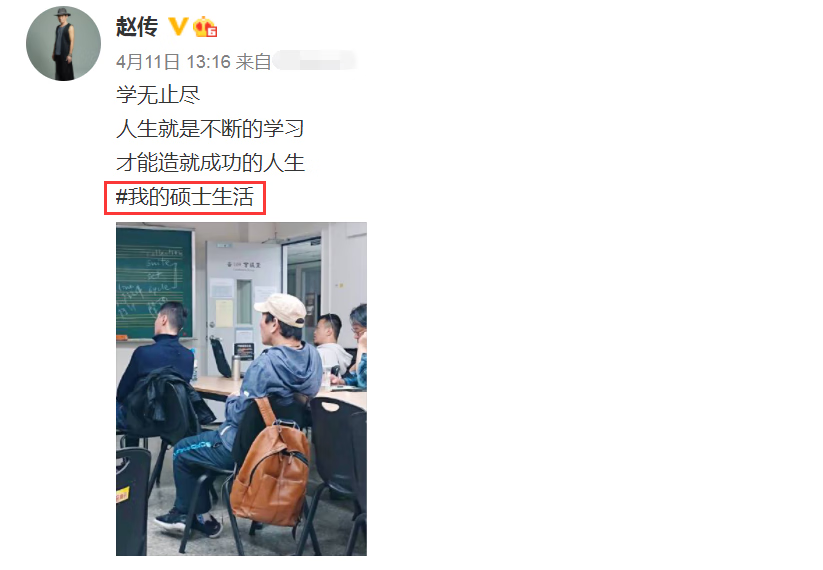作者:Mackenzie Nichols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早在1997年《泰坦尼克号》上映之前就有了《阿凡达》的构思。卡梅隆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卡普斯卡辛小镇,周围广阔的荒野给了他灵感。后来,他开始以水肺潜水的方式来探索海洋。这些在大自然中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并最终创造了潘多拉星球——《阿凡达》的核心。

《阿凡达》
2009年12月18日,《阿凡达》在美国上映,并随之成为了票房奇迹。十年来,《阿凡达》一直是影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译者注:2019年7月《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超过《阿凡达》登上了全球票房冠军宝座),全球票房超过27亿美元,预算约2亿美元,开启了3D电影制作的热潮。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次娱乐之旅(当然它并不乏惊险刺激),它也让卡梅隆得以探索气候变化、扩张主义以及普遍存在的关于认同与接纳的议题。

正值《阿凡达》上映十周年之际,《综艺》杂志邀请到了影片的多位主创谈论这部电影是如何诞生的。
詹姆斯·卡梅隆在1995年写了一个长达100页的「剧本论述」,详细描述了潘多拉星球的视觉世界,并去掉了一些包含对白的场景。他把它带到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但直到《泰坦尼克号》上映的几年后,他才回到了这个项目。他需要技术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来实现他雄心勃勃的愿景。2006年,他终于得到了福克斯的支持,同年他完成了剧本。
卡梅隆:1996年,在我们开始制作《泰坦尼克号》之前,我们做了初步预算,并开始研究数字化可行性。后来有好几年,《泰坦尼克号》几乎完全占据了我的生活。直到我看到人物的面部表现和动画特效有了显著的进步,我才真正回到这个项目中。

《泰坦尼克号》
乔恩·兰道(制片人):我最开始读到卡梅隆的剧本论述时,就爱上了它。当我们开始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使用大布景和时代服装制作老式电影了。那时我们还没有达到数字化的高峰。读《阿凡达》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哦,天哪,这是讲故事的下一波可能性。」
饰演男主角杰克·萨利的澳大利亚演员萨姆·沃辛顿经历了两次试镜,还和已经确认出演涅提妮一角的佐伊·索尔达娜一起试镜。

兰道:我们给沃辛顿打了电话。当时已经搭好了一些布景,我们让他和佐伊一起试戏,萨姆扮演这个脆弱的人的能力以及他在试图召集部队进入战斗时所表现出的力量,以及能够跨越各种表演风格的能力,让我们坚定了这个选择。

卡梅隆:我记得当时说过,「我要追随他上战场、下地狱。」其他人不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想那算是发令枪吧。
佐伊·索尔达娜(饰演 涅提妮):我一直觉得从一开始我就和萨姆有某种联系。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和他一起读剧本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在和杰克·萨利说话。

南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保罗·弗罗默创造了「超越克林贡语」的纳美语。他结合了各种方言,比如波利尼西亚语的声音,以及各种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非洲丛林人的语言,创造了独属于这部电影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交流方式。
卡梅隆:弗罗默把很多奇怪的声音组合在了一起,我觉得演员们不可能掌握它,所以我们回头继续研究,然后开发出一种音谱——一种由基本音素和声音组成的辞典。然后我们的选角导演玛格莉·辛姆金拿了一些磁带和音素来测试每个演员。如果演员不能完成测试,就无法入选。
西格妮·韦弗(饰演 格蕾丝·奥古斯汀):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它确实使用了很多不同的发声方式。我必须说,我非常感激保罗和我们的语音教练卡拉。佐伊的纳美语说得太棒了。更令人惊奇的是,吉姆(卡梅隆的昵称)创造了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语言、生物、植被、漂浮山脉的景观,你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吉姆创造的。语言只是它的一部分。

在拍摄开始前,演员们前往夏威夷进行排练,并与大自然接触,为他们的角色做准备。卡梅隆想让演员们感受爬山、生火和穿越浓密灌木丛的感觉。
韦弗: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互相了解,而且和吉姆待在一起,他可以给我们讲述潘多拉星球的方方面面,还有纳美人的故事。我们和一位植物学家一起旅行,他帮助我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专业的外来植物学家。乔·大卫·摩尔和我去考艾岛的森林采集植物样本。即使它们是土生植物,我们也尽自己所能地学习了这项技术——如何在野外保护载物玻璃片并拍照。这是为了训练我们以植物学家的眼光看待事物。我认为这是无价的。

卡梅隆:萨姆·沃辛顿穿着护裆、缠着腰布到处跑,而且他全身几乎是纯白色的,因为他两年没见过太阳了。他戴着假发,还有头巾,看起来很滑稽,他还拿着弓和箭,有一次他绕过小路的一个拐弯处,也可能是穿过灌木丛,走到小路上的时候,有个人在遛贵宾犬。山姆本能地拉起弓,差点射到狮子狗。他太入戏了。那个人说:「你在干什么?」萨姆回答:「我们在拍电影呢,伙计!」
我们在森林里呆了大约三天。我们清理鱼,切水果,准备饭菜。我认为这对演员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他们可以感受如何行动,以及在如此接近自然的环境中生活是什么感觉。

索尔达娜:我们能够感受土地和雨,感觉到有多冷、有多滑,当你跑步或跳跃或做任何事情时,你需要离地面多近,以及在雨中生火有多难。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进入片场之前所接触的,我们以一种更加尊重的方式去接近纳美人的生活。这是吉姆能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预演。
卡梅隆要求他的演员们想象——他们进行大部分拍摄的摄影棚,本该是遍布茂密的热带雨林和漂浮的山脉。他使用「表演捕捉技术」拍摄演员,然后用数字技术将他们转换成蓝皮肤、四肢修长的纳美人。

兰道:《阿凡达》没有一个画面是在真正的丛林里拍摄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演员体验丛林,然后回到洛杉矶,把同样的感官记忆应用到表演捕捉的舞台上。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对于纳美人和「阿凡达」,我们需要让它们具有关联性。这不是一个「让我们创造一个独眼巨人或怪物」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但又能引起共鸣。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下意识地认出涅提妮背后的佐伊·索尔达娜,看到她们的表演。

韦弗:让我着迷的是,它就像一个空旷的大舞台。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他们放进去的代表虚拟世界的东西。所以他们做了一块木板,让我们体验在森林地面上行走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奇怪的木质延伸物之类的东西来代表树木。
如果你扮演一个纳美人,那么在屏幕上看到你的角色化身或是「阿凡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它向你展示了事物的规模和镜头会是什么样的,并告诉你这个世界的背景,所以你可以想象颜色、森林、山脉或任何东西。

索尔达娜:在屏幕上看到草图和虚拟场地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它们能帮助你更快地想象和理解潘多拉星球。吉姆非常慷慨,为我们提供了任何他能提供的资源,这样我们也才能让潘多拉星球生动起来。
对韦弗来说,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可能是纳美人骑着他们的「灵鸟」在天空翱翔。这个世界的发光生物体,包括水母一样发光的「树精灵」,也让兰道感到震惊不已。

韦弗:我们确实有一个浮在空中的、像马一样的木制品(模拟「灵鸟」),这是非常实用的,当然也给人一种可以自由翱翔和俯冲的感觉。我们不会让演员浮在30英尺高的空中,但所有这些动作都可以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被体验和捕捉到。我们不会像彼得·潘那样飞,那都是后来才有的。但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可以观看回放,看到我们在群山中疾驰,在瀑布中俯冲。
索尔达娜:当然,一开始你会感到眩晕,因为这是团队制作的木制工艺品,但当你真正开始拍摄,吉姆说「开机」,你立刻就进入了这个场景。在经历了几乎失明的那一刻之后,你觉得自己似乎身处潘多拉星球。我们会接触很多东西,比如「灵鸟」的上身——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我们爬上去,他们会把它组装好,然后让它动起来,这是非常难以置信和令人惊叹的。

兰道:发光生物体和「树精灵」第一次落在杰克身上的场景,让我也想要在场。我想去那颗星球,仰望着这些颤动着发光的美丽生物,它们缓缓降落下来,包围着我。这个有着发光生物体的世界是由计算机绘图艺术家创造的。
演员们每天在表演捕捉时穿的黑色套装非常舒适。他们戴的头盔上有两个摄像头,以便能看到屏幕上的特写镜头。最终,表演捕捉技术让观众能够真正地把演员当成他们自己,只不过他们进入了纳美人的躯壳里。

韦弗:套装一边有一条绿色的条纹,另一边是粉色的,还有一些小灯泡,用来传达不同的信息。这些套装穿上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而且穿上后会觉得很舒服。我们的头盔上有两个摄像头,都是面向自己的。我只能想象(它们)是世界上最不讨人喜欢的镜头。这些镜头可能更能近距离看到我们真实的面部表情,以便将其融入虚拟世界。吉姆非常想展示这是一种基于演员的技术,没有任何东西会被动画化。这一切都来自于演员的情绪、动作和面部表情。我认为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是,当电影上映的时候,人们仍然不理解——我不确定他们现在是否理解了——因为有人对我说,「哦,所以你需要给另一个人物配音」,我只能回答「不,不是这样的。」
索尔达娜: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不是很舒服,因为头盔戴着不舒服。甚至让人有点头疼。而鞋也不太合脚。但是一旦你进入片场,开始练习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排练的东西,有吉姆作为指导,这就成为了一种惊人的表演捕捉形式。

卡梅隆和潘多拉星球的缘分未尽。他计划至少再拍三部续集,《阿凡达2》将于2021年12月上映(译者注:目前该片档期已推迟至2022年12月)。
兰道:演员需要在水上和水下来回拍摄,我们制造了一个90万加仑容量的水箱。训练演员的屏气能力,我们希望能让观众因此有更好的观影体验。
卡梅隆: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计划通过四部电影来展现整个世界。我们已经为这四部电影写好了剧本,安排好了演员阵容,我们已经捕捉了第二部电影、第三部电影以及第四部电影的第一部分的表演。实景拍摄已经基本结束了。这个春天我在新西兰待了几个月,所以我们的计划已经步入正轨。
人们还理解不了整个过程的规模和复杂性。这就像是在拍两部半的大型动画电影。一部标准的大型动画电影大约需要4年时间,所以简单计算一下,我们的上映时间大概会是2021年12月。

从生态开发到土著文化的重要性,《阿凡达》不惧处理政治议题。
兰道:我认为最令人心酸的一幕是杰克·萨利被纳美族接纳,脸上被涂了颜料。然后族人们在他身边围成一圈,表示他们接受了他。曾经被他们称为「外星人」的人,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对我来说,我们都希望得到这样的认可。就像你在电影里说「我看见你了」并不意味着我真的看见你了。意思是,「我知道你是谁,也接受你的本来面目。」
卡梅隆:我的素材来源是整个欧洲文明向新世界迁移的历史,无论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还是北美。这是殖民时期的缩影。基本上,征服新大陆是以牺牲所有土著居民为代价的。这是一段漫长而血腥的历史,我想每个人都能看到参照点在哪里。但它同时也是一部环保电影,它将地球上——尤其是热带雨林里的土著居民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自然的看门人和守护者。他们是我们的智慧守护者。他们知道人类应该与自然世界保持平衡的正确方式。
我想如果这种历史真的带来了很多好处,我们就不会陷入现在的困境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在气候问题上做些什么,至少没有及时去做。

在影片上映之后,卡梅隆和兰道说,有少数民族的人找到他们俩,说他们在纳美人身上看到了自己。
卡梅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有其意义,我们从世界各地的环保团体和土著部落得到了大量的积极反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参与了许多土著事务,并试图支持他们的一些事业,尤其是在亚马逊地区。我去过那里几次,参与了一些反对修建大坝的斗争——这些大坝将会摧毁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但十年后,我环顾四周,只看到在生物多样性、森林砍伐、土著权利、文化丧失、语言丧失、海洋污染、海洋温度上升等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抗争几乎在每一条战线上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变得更聪明。

兰道:在电影上映后我去过一次以色列——那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对我说,「乔恩,我看了《阿凡达》,纳美人就是我们。」第二天,我遇到了一些巴勒斯坦人,他们也说,「乔恩,纳美人就是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南美,还是在亚洲,人们都认同这些角色,认同这些文化,并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