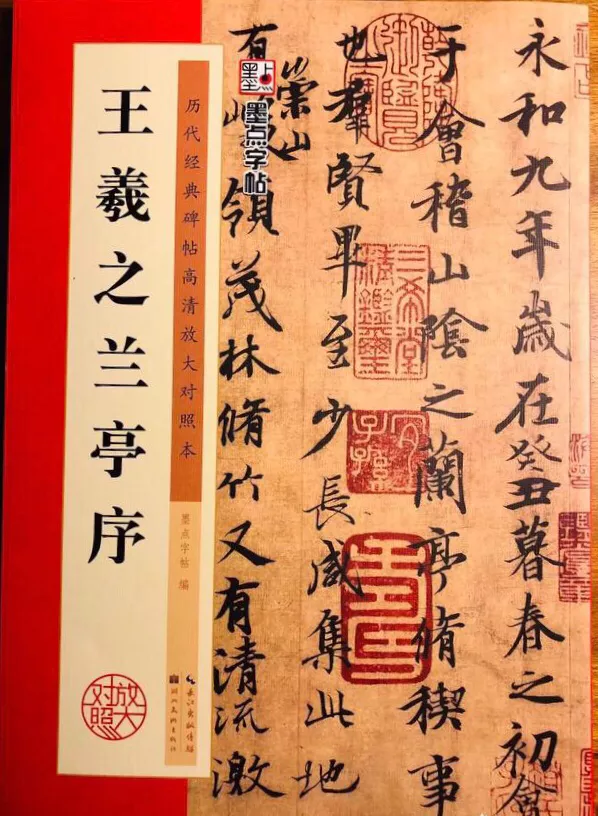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公主是个奇异的群体:在物质方面,她们不仅身具皇家的尊贵,还手握经济实权,在唐朝前中期,公主除了食封制的收入外,还有皇帝平时的赏赐,另外加上出嫁时的嫁妆与夫家的产业——她们是真正的有产阶级。但是更重要的是,唐时期儒佛道交织,精神世界自由斑斓,而且李唐王室在胡化风俗影响下,对女子的教育并不像后期以及以后那些时代那样束缚,而给予她们更为广泛的自由空间。
《新唐书》说她:“主负所爱而骄。”她的时代,是大唐盛世。她的父亲,是当世明君。她的身份,是天朝公主。她的富有,是无数田业。她的宠爱,是“礼异它婿”,她是高阳公主,太宗最宠爱的公主。

史书这么形容她的丈夫:“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不喜欢学问,只爱武力。父亲一向宠她爱她,到头来却要让她嫁给这么一个不如意的男人。
于是,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她没有足够的智慧开解命运的纠结,却有足够的能量怨恨人生——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该怨谁,那么,就谁都怨。
反观她以后选择偷情的那个男人,却以渊博的学识、优雅流利的文采而知名,据说承远祖隐逸之士的血统,自小志向高远,专心学问。十五岁时,出世为僧,在大总持寺成为道岳法师的弟子。至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回国在长安弘福寺首开译场之时,便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被选入玄奘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是时辩机的年龄约当26岁。也因为跟随唐玄奘在弘禅寺院译经,以帮助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而名噪一时。
摆在她面前的敌人,第一位便是自己的“弟媳角色”——丈夫的身份与地位。
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也就罢了,居然还是老二,能继承房家身份与荣誉的,是长子房遗直——“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

自然对于唐朝公主来说,皇室尊严与儿媳身份就是一对矛盾,很多公主在出嫁以后不行姑舅之礼(也就是不向公婆行礼),以公主身份自贵,不尊重家族里的长辈。高宗就曾经为此单独下诏进行劝谏。
显然,对于高阳来说,突然降为一个家族的儿媳、弟媳,是让她最先不适应。对于高阳来说,自己贵为公主,自己的丈夫居然继承不了正统,这显然是不能忍受的,她表现出了不满。房遗直显然得罪不起这位高贵的弟媳,主动提出来让出爵位(其实包含着让出宗祧的意思),而太宗的回答是,不许。
正在穷途茫然之际,命运给了她第二次挑衅的机会。
一个明媚春光的下午,在她与丈夫游猎途中,她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他叫辩机。
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新唐书(卷八十三)》)
在少不更事的少女眼里,这是韩剧式的浪漫邂逅,是帅哥与美女、佛教王子与天朝公主的爱情相逢;

在成年女性眼里,这是陈冲版的《诱僧》,是情欲的禁忌与胶着,是突破礼教束缚欲望突围;
在男人眼里,这显然是一场不要钱还倒贴的、让人羡慕的艳遇;
在宗教徒眼里,这是一场意外的劫难与遗憾,显然,放在辩机的师傅面前,高阳真是个妖孽。
有时候真不知道这样的比较是否高看了高阳与辩机这段爱,只知道起码对于辩机,是无辜而纯情的,他可不是什么好色贪花的野和尚,少年时期是出于对佛法真心的尊敬与仰慕,弃绝尘俗而修行,在佛祖的圣化下希望寻找心灵的净土。可是,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遇到自己人生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公主,一个美丽的公主,还有她的夫婿。
高阳勾引辩机的动因,在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女人眼里,身边的男人这样可鄙,疼爱自己的父亲这样“不公”,只有破碎一切、报复命运、报复自己才能让她产生快感。恰好此时,一个好的道具出现了,一个英俊的男人,而且那个男人是个有才有貌的和尚。
如果,辩机只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也许只会引起高阳的兴趣,但是辩机不仅仅是一个英俊的男人,而且是个和尚,还是个持守清规戒律而才华横溢的和尚,这就足够引起高阳意外的征服欲——禁忌,是那样充满了诱惑的魅力,征服这个男人,仿佛也就戏弄了父亲所给予的命定(婚姻),同时也将是自己魅力的证明。生活如此平凡无味,也许在可以超越禁忌的情感搏杀里,她才能体味生命的那么点激情。

《册府元龟》记载了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的一道诏令,说很多官家跟僧道往来频繁,包括自家妻妾都无所顾忌,于是产生了很多丑闻,因此以后,禁止官员随便接纳僧尼道士在家里住——这条诏令从反面揭示了唐代贵族家庭蓄养僧尼,妻妾与僧尼自由来往的风俗。激情过后,辩机选择了逃避。
贞观十九年正月,唐玄奘得到御准,在弘禅寺院译经,需要助手。他申请去了。他要离开这个女人的势力范围,离开她所给予的温情,他知道,那不是他应该驻扎的地方。可怕的是,高阳公主还投入了真感情,因为,辩机世界里的那份清凉、纯白、庄严,让她忍不住去踏人,去掀翻,甚至去亵渎。是辩机的陌生与禁忌,成全了她的叛逆。可是,他现在要走了,以很多神圣的名义(许多男女分手时,“我为你好,你为我好”之类的废话不必说了),她舍不得。于是,她送了他一个致命的枕头。
高阳送给辩机的,是一个缀满珠宝的枕头,有个好听的名字——“金宝神枕”。这是充满暗示性的东西,效果就像现代情人之间送的名牌避孕套,意味着只有两个人能见到的私人亲密。
高阳的意思大抵是让辩机一看见它,就想起两个人之间的枕间生涯——―如《西厢记》里,红娘抱着莺莺的枕头送她去见张生,“鸳鸯枕,翡翠衾,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也是《洛神赋》前序里的“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

高阳想让辩机记一辈子。辩机要了吗?要了。他不能不要。如果推辞,高阳会给他别的,男人对曾经的女人总有那么几分心软,尽管不爱了情面还是要给的,他接受了。但是,他显然没有藏好,过了几年居然让小偷偷去了。
在与辩机私通的岁月里,她多少平定了那份不安稳的心。从婚姻不如意开始,她本来到处挑衅,突然发现辩机这个挑衅很有意思,于是深入地玩了下去,并且为了玩得更好,她聪明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堵住丈夫的嘴。
史书上说:“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
其实,房好歹也是高阳的丈夫,唐朝尽管开放但毕竟也是男权社会,没有一个有尊严的男人能忍受自己头顶着绿帽子到处跑,而房遗爱居然忍了,而且据说还能提供便利。
只能证明这个男人根本不把高阳看作妻子。他更把她看作主子,看作能给他带来荣华富贵的工具,所以,他欣然接纳了公主补偿性的赏赐——两个美女,并且,也接纳了公主的金钱贿赂。对于他来说,丈夫的尊严大不过皇室的荣耀,现世的享受显然比那些虚幻的气节更加实在些。

辩机在的时候,高阳终于略微平稳了那份叛逆的动荡,可是辩机走了,带走了她的寄托,又还给了她的寂寞,她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房家长子房遗直。
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高阳让丈夫房遗爱去闹分家。如果真要分家,高阳是要吃大亏的,她有自己的“食封”,每年税户都要给她交钱交绢,她给丈夫的封口费就能达到“亿计”——这样的有钱人是最能分家的那个。因为中国实行的继承制度,是“诸子平均”,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对于负责主祭祖先的长子长孙加一份田产——这就意味着一旦分家,房遗直会以长子的名义占有大量的田产。
我们看史书后一句“既而反谮遗直”——原来她的计划是分家以后,诬告房遗直贪图财产,故意分家以侵占。

而《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规定:
“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受,坐赃论,减三等。”——多占家产与偷盗之罪是等同的。
这下我们可以明白了,高阳的计谋并不是要分家,而是要在皇帝父亲面前给房遗直泼脏水,让太宗以为房遗直是个贪财的小人,为了侵占财产,故意以分家的方式“合理性”占有。
她了解自己的父亲,这样“分家”以后,她,高阳公主自然暂时会吃亏。可是他房遗直敢主动“分家”,那就是欺负公主,就是让皇帝吃哑巴亏——皇权尊严不可侵犯,太宗是聪明人,而聪明人最忌讳的,就是被聪明人戏弄。
《新唐书》这样记载:“遗直自言。”
如果高阳计谋得逞,太宗必然对房家长子印象打折。按照常理或者按照高阳对于房家人的推想,房遗直应该是沉默的——她是公主,而且这样的诬告表面看来也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是想分家产而多占一些产业而已。高阳自己觉得自己了解父亲,但是并不认为房遗直了解,在她眼里,房家都是些面瓜。

要知道,在一个臣子的眼里,没有比得罪皇上更严重的事情了。房遗直还不想那么快就去见刚去的老爹,他宁肯得罪公主,也不能让皇帝对他心怀成见。他干脆主动告诉了太宗。
太宗什么反应呢?《新唐书》上说“痛让主”,《资治通鉴》亦言“深责让主”。都是重词,而且后面都紧接着变化语:“自是稍疏外”,“由是宠衰”。
不久,长安城里出了一件大事,御史审盗,审出一个惊天的秘密丑闻——一个小偷的赃物里检查出一只皇家枕头,而枕头的来源,是译经高僧辩机的房间。
结果辩机很快跟审案的御史说,这是高阳公主赐予的。
要说唐朝贵妇偷情或者跟和尚道士的私通,其实数不胜数高阳与辩机的事情如果是私下里处理,也许不会这么严重而惨烈。可惜,那只枕头惹祸了,它经过了小偷的放大,又经过了御史的放大,满城鼎沸,成了公众面前的一件桃色新闻——公开侮辱皇家颜面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过。
太宗大怒。
女儿不懂事也就罢了,居然去跟一个和尚私通,而且这个和尚还是自己从前深为赞赏的。满朝文武、满城百姓面前,皇家颜面何存?房家颜面何存?太宗大怒,辩机被判腰斩,“杀奴婢十余”,高阳彻底失去了父亲的爱。

她的辩机死了,她心里唯一的寄托,现在也烟消云散了。现在,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剩。那个一向疼爱的父亲不仅让她嫁给了不爱的人,还杀死了她唯一的爱人,包括,身边朝夕相处的侍女。
父亲也不再见她,她的眼泪不管用了,也不再理会她的悲伤。本来最疼爱她的人,却亲手把她推向了地狱,她突然感到了人生的崩溃。
不久,太宗去世了,她视之为仇恨目标的那棵大树轰然倒塌。这个世界,辩机去了,父亲去了,极爱的和极恨的,极恨的和极爱的,都离她而去,只留她,孤单单。
而正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出现在她面前,提出了一个恳求,希望她看一下宫内“機祥”,她答应了。
她买通宫内宦官“伺宫省機祥,步星次”,看宫中天象,预测宫内的天机,并把自己的占卜结果告诉房遗爱……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皇亲国戚们某些不满的发泄而已,其实并没有事实上的谋反行为。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让闹剧成了悲剧。
关于这件事情,《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
房遗直是个聪明人,高宗上台,正要杀人立威,二弟却跟那些不满的皇室往刀口上撞,那个骄横的弟媳妇又天天跟些和尚道士鬼混——这也就罢了,居然还找宫里人看什么天象,这将会发生什么,房遗直心里很清楚。
当时高宗把这件家庭纠纷案交给长孙无忌审理,结果审成了政治案。他们的怨言成了谋反的铁证,涉案的主犯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要被判死刑,牵连的李元景、高阳、巴陵等要被赐自尽。长孙无忌根本不是要处理家庭官司,而是要趁机歼灭政敌。
长孙无忌找到房遗爱让他诬陷李恪。因为长孙跟李恪是有深刻矛盾的,《旧唐书》记载,太子承乾得罪,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
现在长孙掌权,自然想除掉这个眼中钉,“以绝众望”。

他以为,他的诬告可以换来苟生,可惜他想错了,跟薛万彻们一样,他同样被押赴刑场,同样被处斩而高阳公主被当成从犯赐自尽。
高阳接到了赐死的诏书。死亡终于让她彻底清醒,生命之不能承受的,是太过轻易地得到,是太过自我的放肆,是无以贯穿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她这辈子,太轻,太轻。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